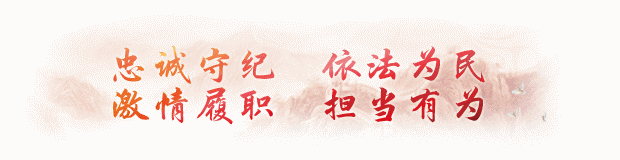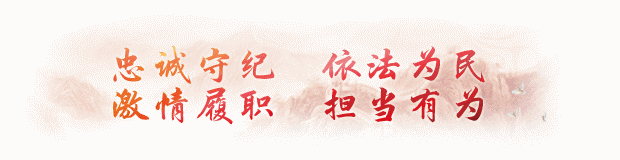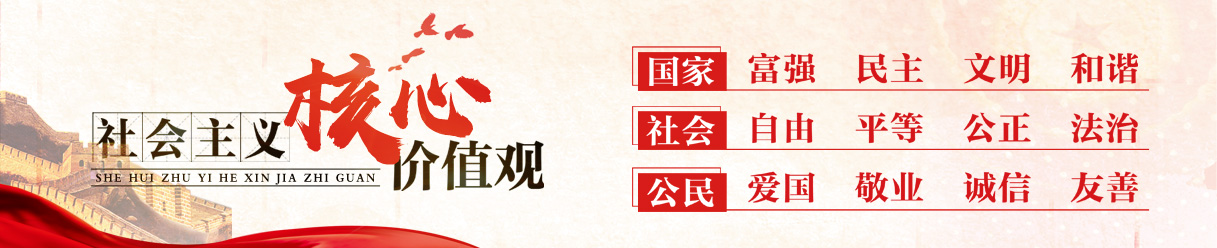和谐社会“呼唤”制度公平
发布时间:2007-06-29 阅读次数:1485
和谐社会“呼唤”制度公平
刘风霞 顾庆华(山东 青州)
如果说某人在某种环境中宁愿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那一定是迫于无奈,甚至是受到人身威胁,因为不论何种情形,生命才是第一位的!更何况当某些司空见惯的个别不公平不公正“待遇”麻木了人们的思想,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然。于是,当农民工不准进北京市的某公厕时,他们忍了,因为那儿的“制度”规定:公厕是为附近的居民、出租车司机准备的,农民工不讲卫生;宁波某风景区的警示牌明示:衣冠不整着、拾荒着、农民工等不准入内,“不止步者后果自负”,他们能不忍吗?因为这儿的制度更明确,“后果自负”的警示足以让这些弱势人群望而却步;至于大学校园不让某些人进入,机关办公场所不让某些人驻足;同样拿着一元钱的乞丐因“身份问题”被公交司机撵下车……等等,不一而足的歧视性规定和言行,与其说是对某些人人格尊严的蔑视和不公,倒不如说是对民主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审视和考量,因为它使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的杂音噪音不断,甚至于“依法”人为地划分了人的身份层次,人为地制造了高低贵贱之分,人为地制造了社会矛盾、破坏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与秩序,而我们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没有给予“某些人”有力的保护,致使他们的合法权益或要求遭受到了不应有和不公平的冷遇。
诚然,“无规矩难成方圆”,但倘若我们的某些制度、规定以“规矩”某些群体,甚至是弱势群体言行而使另一个群体取得一种居高临下的“主人”般的优势或优越感,这显然有孛于我们制度制定的初衷,显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圭臬。
我们不妨把“公平”的镜头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来看,法律、制度公平之于社会主义的内涵,当然不只是人格尊严歧视的问题。比如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市民要比农民赔偿的多,虽然严格执行了法律规定,却明显昭示市民的命比农民的命金贵,问题出在哪儿?政策设计的开始就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那就是按城乡不同的收入赔付亡者。据《潇湘晨报》报道,公交车超车摔死乘客蔡某,因死者为农业户口,经长沙两级法院两次审理,陪偿金由19.7万元降至8.6万元。难怪死者之子发出 “农村人的命就比城里人的命低一等吗”感叹。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公平之上的新的不公平,农民不但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农补工”推动着社会的进步,造成城乡“收入” 的差距到死却也无法站在一样的起跑线上。试问,责任的板子这样打在农民的身上,不知道法律制度政策制定者是处于何种考虑?还有如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否恩泽了更广大的群众,是否从人人享受同等的权利出发,而城镇居民享受着80%的公共卫生资源的现实告诉我们,屡见不鲜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人群提醒着我们,这些方面的制度公平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不容盲目乐观。
毫无疑问,制度公平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是我们为实现现代法治和民主社会而孜孜追求的目标之一,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基本条件和要求。我们有理由期待,随着法律制度制定从源头上对公平正义理念的践行,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团结友好、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将逐渐成为我们的现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