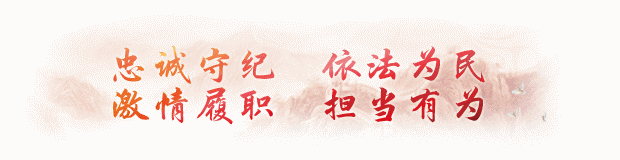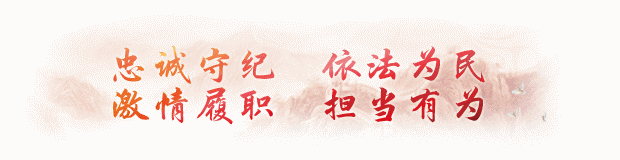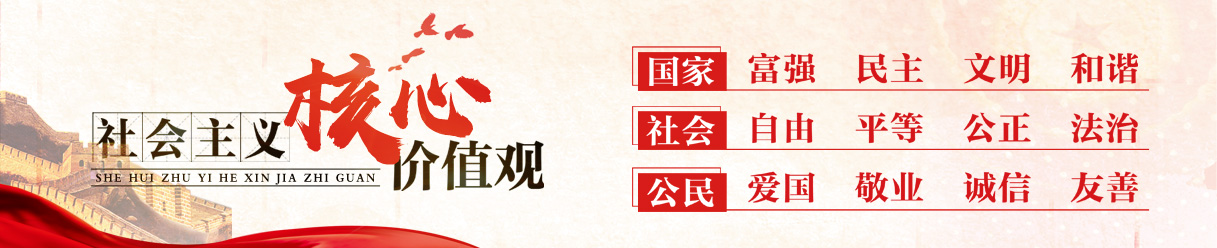人大要敢于说“不”
发布时间:2007-08-24 阅读次数:1565
人大要敢于说“不”
付文广
人大作为法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从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的规定来看,其权力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确认性或曰肯定性的认可权力(说“是”),另一类是纠错性或曰否定性的监督权力(说“不”)。过去,总体上说,人大在人们心目中说“是”的时候较多,说“不”的时候较少。当然,说“是”也好,说“不”也罢,都必须是有原则和底线的。这个原则和底线就是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把党的政策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因此,毫无疑义,人大对党的正确主张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是”,使其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同理,对于那些掌握着一定公权力的部门或个人明显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也要理直气壮地说“不”,从而监督公权力姓“公”,防止和杜绝公权的腐败。倘若在应当说“不”的场合,人大却没有说“不”的勇气,说的严重一些,这是党性不足的表现(指对人大代表总量中占据多数的党员代表而言),也是对法律的尊严和正确实施漠视的表现,更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负责任的表现。客观地说,人大监督职能的发挥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社会上对人大是“橡皮图章”和“缺钙”的刻板印象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建设“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的观念已经逐渐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透明行政、责任行政”理念日益昌明的形势相适应,作为监督“一府两院”的更重要公权力部门,人大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化与“可问责化”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打造一个“透明的人大”、“可问责的人大”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法第14条第二款、第20条第二款、第27条第二款分别就①人大常委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②常委会听取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③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其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作了专门规定。笔者认为,《监督法》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以及“一府两院”落实整改意见的情况向社会公开是改进人大工作、树立人大新形象乃至于提升人大权威或曰合法性的重要契机。原来饱受舆论诟病的人大“缺钙”现象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根本扭转。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人大在借助各种媒体向社会公布人大履职尤其是履行监督职能的情况,以及引入市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尝试让人大权力运行过程透明化的做法有利于将人大监督与新闻媒体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监督合力。例如,1999年1月贵阳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决定,从第11次会议开始,贵阳市民可以自由旁听常委会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到2001年9月第32次常委会会议为止,全部21次常委会会议都实行了该制度,参加旁听的市民超过200人。这种市民旁听并发言的制度系全国首创。据悉,实行这一制度后,人大的工作与广大群众的距离拉近了。其次,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执法检查质量提高了。一方面,由于有市民的旁听,人大常委的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另一方面,在立法和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市民的参与起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再次,人大的监督得到了落实。由于有市民旁听并有市民发言,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从过去的谈成绩变成了谈问题。例如,在第32次常委会议上,市政府有两个局的候任局长的供职报告没有通过。最后,旁听还具有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市民以及部分干部对国家权力结构的运行、重大法律规定有了深刻的了解。市民的政治参与能力通过发言也得到了训练和提高。此外,市人大常委会的市民旁听制度还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贵阳市各区县的人大常委会已经在2000年开始陆陆续续实行了开放市民旁听并听取市民发言的制度,省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9月也作出了从第9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开始开放公民旁听的决议,上海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大常委会也积极引入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又如,2003年9月2日,由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温州新闻网和《温州都市报》联合主办了《代表在线》栏目,以报纸版面和网络对话两种形式穿插出现。《代表在线》栏目两周一个选题,隔周二的《温州都市报》以整版的篇幅,对所确定的选题进行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温州新闻网邀请人大代表、政府部门领导及相关专家、学者与网民进行网上直接对话,次日的《温州都市报》再以整版的篇幅刊登经过整理的网上聊天内容。对一些事关全局的问题和意见以书面或其他形式转交相关的部门办理落实。这样,人大的履职行为也就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人大作为监督机关实际上面临着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压力,这无疑可以促进人大自身勤勉履职,从而不负选民的重托。从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看,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解决和回答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
从法理上看,人大虽然是法定的监督机关,但是,基于选民与代表的权力委托、代理关系,人大本身应当接受来自选民和社会的监督应毫无疑义。换句话说,法律一方面赋予人大以广泛的权力,另一方面,根据权责一致的原理,人大行使职权也是其不可推卸的法定职责,这就需要社会(选民)加以监督。人大工作的好坏,唯一的评判主体只能是全体选民。著名人大研究专家蔡定剑教授说:“人大是个民意机关,它手中没有‘钱’,也没有‘剑’,它的力量从何而来?从人民中来,从法律中来,从社会中来……正由于此,人大的监督就不能仅仅靠人大代表本身,而要借助于各种社会力量和各种国家机关的力量”(蔡定剑:《为温州市人大开办舆论监督节目叫好!》 见《代表在线》胡经琨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如果人大与社会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联结和互动,人大的运行过程不能做到透明化,选民对人大依法履职的问责机制不能有效建立起来,那就很难真正避免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出现“软刀子割肉”的窘境,人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